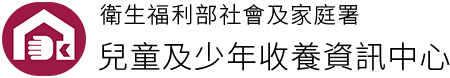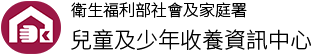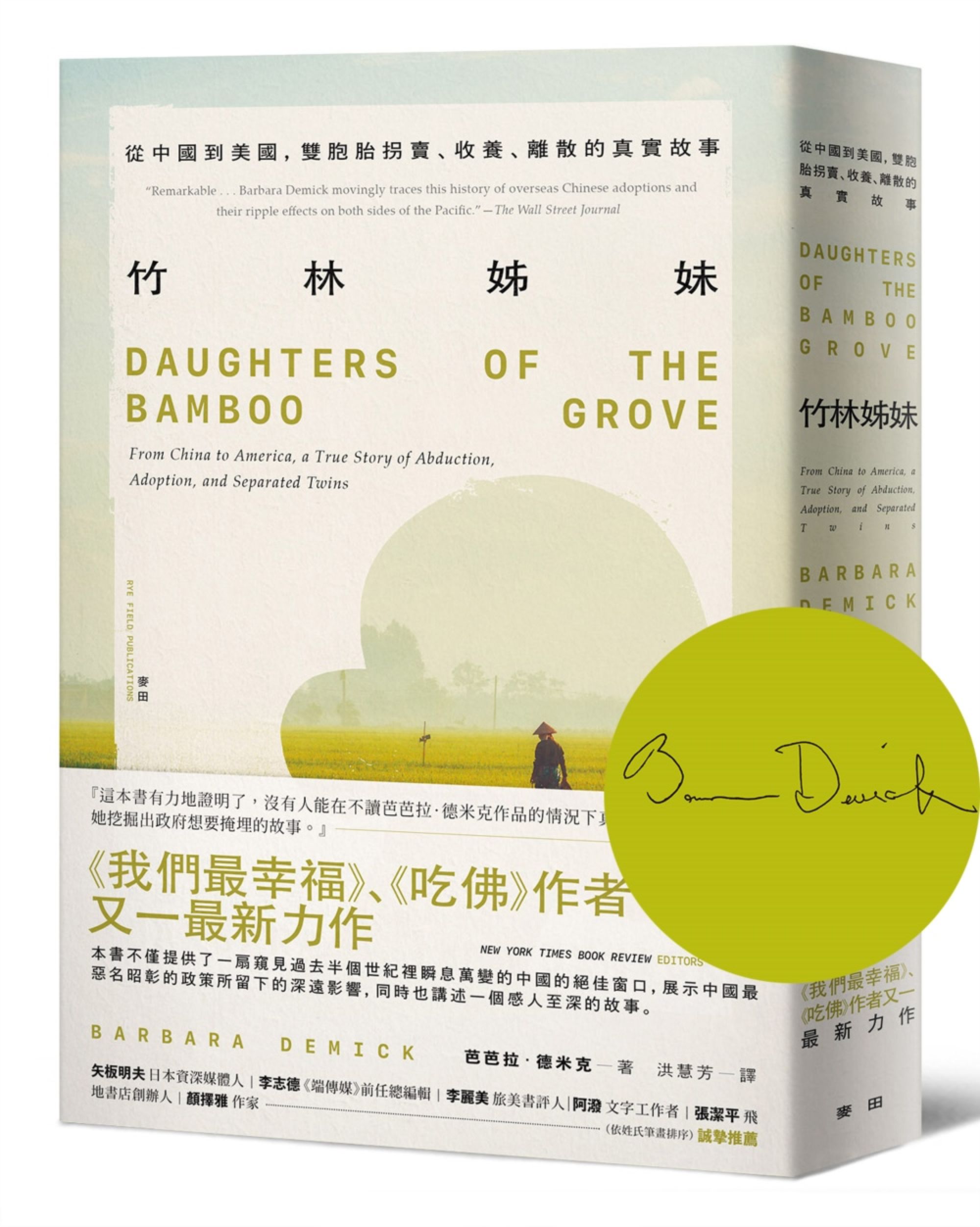
超乎想像的一胎化鬼故事(沒有鬼的那種)──讀《竹林姐妹》
超乎想像的一胎化鬼故事(沒有鬼的那種)──讀《竹林姐妹》
【114/10/30】博客來作家專業書評/作者鄭進耀
我的某位中國朋友因為是家裡「超生」的孩子,加上又是女兒,於是她沒報戶口,以黑戶生存在鄉間,連名字都沒取,長輩乾脆就叫她多餘。「多餘」向我說起往事,語氣帶著自嘲,臉上帶著笑意,眼神卻透著對自己的不捨。
讀了《竹林姊妹》更確認「多餘」並不是特例。這是一本關於一胎化的鬼故事,沒有鬼的那種。
1979年開始,中國勵行節制生育政策,每對夫妻只擁有生產一胎的權利,未婚者甚至無法生育。然而,數以千萬計超生、黑戶小孩,究竟去了哪裡?作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追蹤一對在2000年超生的雙胞胎,她們的母親袁贊華為了規避追查,躲到親戚家。最後,在竹林產下一對雙胞胎姐妹,曾芳芳與曾雙潔。
身處台灣的我們很難想像,不過就多生幾個小孩,是多大的事呢?不,是很大的事。
超生的孩子去哪了?
以執行規模來看,光生育控制的人員就很驚人,「到了1990年代,據估計有多達8300萬人至少兼職參與計劃生育工作(當時中國的軍隊總數不過300萬人)。計劃生育部門還招募退伍軍人來擔任執法人員,這些身強體壯的男人受過維安訓練。」
這群人在路上盯著女人的肚皮,監看誰家又生小孩,甚至引入地方的流氓出手教訓這些「逆民」。主要的合法手段是要求超生的夫妻上繳罰款,而這個金額通常是農民二到六倍的年收入。不服者,則遭痛毆,搶走孩子。
更多是踩著道德邊緣要求孕婦墮胎。中國調查記者袁凌在《青苔不會消失》裡描寫一名老人,因年輕時被強行墮胎,最後傷及身體,終身佝僂,只能彎著腰行走。
《竹林姐妹》則更進一步指出各種殘忍的細節,比如嬰兒已經成形,還是要強行催產。要趁嬰兒的腳還沒脫離產道之前,直接在嬰兒的頭骨蓋注入甲醛,毒死胎兒。一旦胎兒離開母體,那就是謀殺。雖然在這個例子裡,兩者差異並不大。
這不只是個人的為惡,還是體制集體支撐這樣的惡行。超生的罰款成為地方政府重要收入來源(從1980年代開始,罰款總額超過3140億美元)。地方政府每年設立出生人口數,一旦超過這個數字,控制生育的相關人員都要連坐處罰;相反地,如果成為國家的「生育示範區」,公務員可多領20%的獎金。
執行一胎化可以增加地方收入,因此有了政策誘因;再加上執行者因連坐法被集體綁在一起,增強了執行力度。最後,生育控制猶如潰堤洪水,如入無人之境。
對於80到90年代人口眾多的中國農民來說,中國政府的言論控制與他們無關,他們不看報紙,也買不起電視。人民移動的限制也與他們無關,反正他們沒錢出國。甚至,他們窮到連稅都課不到,也不會像天安門事件裡的人們上街爭取民主自由。
天高皇帝遠,遠在天邊的皇帝什麼都管不著,只有生育這事,管得特別沒道理。一胎化是中國底層農村最直接的惡夢。
這個惡夢如果只有罰款、毆打超生夫妻與強行墮胎,尚不致於成為一則鬼故事。出人意料的轉折是,這個國家有系統的強行搶走這些孩子,書中的雙胞胎姐姐袁芳芳便是被生育人員從家人的懷裡搶走,從此下落不明。
袁芳芳只是那個年代成千上萬被搶走的超生兒的其中一個,芭芭拉追查這些消失的孩子,意外發現,他們都在各地方的育幼院待過,再由外國人收養。
90年代,中國「出口」這些孩子,並將他們視為與西方世界的「連結」,未來有機會報效「祖國」。他們建立一個看似透明的機制,育幼院的孩子都會先在地方報紙上公布走失消息,一段時間沒親人認領,便開放外國人收養。
每個收養機構向收養父母收取3000美元「捐款」,這筆經費則轉做地方福利事業。收養中國棄兒對當年最大收養國美國來說,這滿足了他們「西方救世主」的自我想像。同時,中國農村孕婦通常沒有酗酒與毒品問題,意味嬰兒的健康品質更佳。對他們來說,收養中國兒童是性價比很高的選擇。
尋親與自我認同困境
90年代的美國社會以領養中國女童為潮流,甚至時尚雜誌也以此為主題做過報導。
如果,事情是雙贏的狀態也不會成為鬼故事。這些被美國人收養的女兒們長大之後,有人想回中國尋親,過程讓原本溫馨的親情故事瞬間成為國家罪行的鬼故事。
因為他們發現,育幼院刊登在當地報紙的「尋親公告」大部分是假的,例如,一處輪胎行門口竟然前後有十個棄嬰與走失兒童,簡直是嬰兒聚寶盆。再往上追溯,這些被認養的小孩都是國家有系統從超生的父母手上搶來,再轉交給當地育幼院,他們藉由出養兒童坐收暴利。國家特別挑上那些地處偏遠、父母離家打工、識字有限、獨留老人看守的家庭下手,因為這是最不會反抗的一群人。
那些當年執行生育控制的人很可能也分享了部分利益,書中提到一位鄉下產婆,疑似是當年通報曾家雙胞胎的人,以助產為業的她在鄉間擁有一間豪宅,資金來源十分可疑。
尋親也不是 DNA 配對這麼簡單而已。對於被出養到國外的這些「女兒們」,有人終其一生找不到親生父母,有的害怕二度遺棄,被親生父母拒認,而不敢踏上尋親之路。更多的人,則是處於複雜的幽微心情:中國父母會把我要回去嗎?我要養中國的家人嗎?我的養父母會不會覺得我背叛他們?
這些出現在90年代時尚雜誌的熱門中國女孩,長久以來面對異文化的自我認同問題,尋親又讓一切更顯複雜。作者芭芭拉找到了出養到美國的曾芳芳,此時,她已是名為「以斯帖」(Esther)的美國少女。書裡描寫了雙胞胎姐妹重逢時,想要表現熱絡卻又是陌生人的尷尬情景。
《洛山磯時報》用影片紀錄了以斯帖重返中國與家人重聚的影像,那已是六年前的影片,重逢的場合令人感傷。當年手上抱著以斯帖、讓小孩硬生生被搶走的舅媽在畫面一角,哽咽得說不出幾句話。在故鄉裡成了異鄉人的以斯帖最後和妹妹在房間裡,玩起了拍手遊戲,這是留在中國的妹妹雙潔的願望: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姐姐一起玩。而這個願望實現時,姐妹都已是成年少女了。
A Stolen Twin Reunites with Her Birth Family
一胎化如何影響這一代年輕人?
失去子女的父母,和返鄉已成異鄉人的女兒,這些惡夢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方鳳美的《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剖析一胎化能執行長達36年(1979年至2015年)是因為中國的專制體制,政策的形成是由上而下(竟然是由一位火箭專家主導),欠缺民主化討論。執行過程也缺乏彈性修正,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對這個失誤的政策喊停,生育控制政策甚至還被寫入中國的憲法裡。
一胎化的惡夢如何影響這一代的年輕人?有人像以斯帖這樣身在國外、為自我認同與認親所苦。目前國際趨勢已不再鼓勵這類跨國認養,以避免小孩跨文化的認同適應問題。而沒有像以斯帖被「賣」到國外的一胎化孩子們,則面臨另一種挑戰,他們承接了三代的期待壓力。方鳳美在美國任教,她觀察到一胎化的這一代並不如外界所說「集三代寵愛」成為家中小霸王。相反的,他們為回應整個家庭將所有資源投入獨子養育的期待,反而只敢追求保守穩定的選擇,人生只求安穩平凡,一點也不狼性。
方鳳美引用學者研究,一胎化對GDP成長的影響甚至不到1%。《竹林姐妹》引用的資料也認為,就算沒有一胎化,中國的人口問題也會隨著都市化與經濟發展得到自然解決,人為強力介入最終造成整個世代的集體傷害。
《竹林姐妹》裡著墨較少的曾雙潔,這種隨父母到城市打工,因沒有戶口,受到較差的照顧資源,稱為「流動兒童」。至於,父母把小孩留在農村給長輩照顧的,則成了「留守兒童」。
中國調查記者袁凌長期關注留守兒童,他在《青苔不會消失》引用學者張丹丹的犯罪研究,這群父母離家打工,將小孩獨留農村,衍生許多教養問題。留守兒童長大之後,有強烈的不平感(對自己被留在農村感到不平),這些不平感沒有得到好的引導,最終成為暴力犯罪,張丹丹的獄中訪談,有極大部分的犯罪者都有留守兒童的背景。
那些隨著父母打工來到城市的「流動兒童」,沒有好的教育資源,父母也忙於工作,疏於照顧。袁凌談到,有些男孩在青春期就到街上成了「飛車黨」,在城市惹禍後又被送回農村。回到農村,他們與當地的女孩談戀愛,這些女孩多半是留守兒,渴望被愛。這些男孩以愛為名,逼她們從事色情產業來供養自己。
留守兒童不見得都會成為罪犯或受害者,這些不平感若有合宜的引導可以成為正義感。袁凌本身也是留守兒童,他曾在podcast(「忽左忽右」EP314:被剝奪的童年)談到一位律師,也是留守兒,對不公平的事特別在意的她成為好律師,但童年經驗讓她在兩性關係上有極大的障礙。也有統計,留守兒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比例在成年後患憂鬱症。袁凌在節目上說:「這個創傷他們要用一輩子來療癒。」
中國青年的「心靈危機」不只在底層。2015年北大學生吳謝宇殺了母親,將母親屍體放在老家,並在老家裝監視器,還在屍體四週放置防腐劑。《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群追蹤此案寫成了《人性的深淵:吳謝宇案》,詳細描寫上一代文革的傷害、貧窮的中國社會,如何細微地將創傷傳入下一代的獨生子。看似出人頭地的吳謝宇進入北大之後,開始面對各種生活挫敗,經濟、出身不夠頂尖,無法覓得好的實習機會,也無法出國當交換學生。只會「刷題」進入頂尖大學的他,當成績不再頂尖,便失去活著的意義,他的各種挫敗經驗,最後扭曲成殺母的結果。
我們不只在《竹林姐妹》讀到一胎化的惡行,還在不同的非虛構作品如《青苔不會消失》、《人性的深清淵》讀到當代中國的各種鬼故事,這些從來不只是個人的困境,而是整個中國獨特的體制餵養出這些不公不義。
中國現代化的城市建設、壯麗的山河與民間小吃都是肉眼可見,但存在中國人內心創傷的鬼故事卻被藏在深處,難以言說。畢竟,鬼從來不是輕易可見。
出自:博客來
延伸報導:報導者 《竹林姊妹》從失蹤女嬰揭露跨國收養真相:中國孤兒院如何成為販嬰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