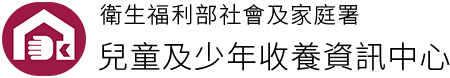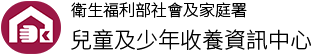“在 42 歲時,我明白了為什麼我的母親放棄了我的收養”
2022/08/25 【Luo Yun】
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從愛爾蘭收養的,但當我終於在 30 歲出頭時看到我的出生證明時,我仍然沒有做好準備。
看到我母親的名字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知道她是一個真實的人。 它把事情放在了正確的角度,我不僅僅是費城那對撫養我長大的夫婦的產物。 那裡還有另一個女人,她 1960 年在愛爾蘭生下了我。
我能夠通過美國的信息自由請求獲得我的出生證明。 但將於 2022 年 10 月生效的新《出生信息和追踪法》將意味著所有在愛爾蘭出生並在國內或國外收養的人現在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訪問他們的出生證明和記錄。
許多人現在將有權獲得他們以前從未有過的信息,儘管他們是否將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並與他們的親生父母聯繫將取決於他們。 這是我在 80 年代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時做出的決定。
一個“田園詩般的”童年
我出生在愛爾蘭的貝斯伯勒母嬰之家,一個 26 歲的未婚女性,在我 18 個月大的時候被費城的一對夫婦收養。 我是在愛爾蘭出生並在美國收養的 2,000 多名兒童之一。
瑪麗·斯蒂德和她的養父母在費城。 斯蒂德說她的童年是“田園詩般的”,但她覺得自己不適應。
我被收養並不是什麼秘密。 我很高興我的父母對此持開放態度,因為它消除了後來發現的心碎。
在許多方面,我在費城度過了一個田園詩般的童年。 我父親擁有一家管道和供暖公司,所以我們過得很富裕。 我的兄弟——他是從貝斯伯勒單獨收養的——我和我被送到了好學校,我們被鼓勵去上體育和音樂課。
這是我親生母親當時無法給我的機會。 但是,我認為收養不是更好生活的保證,而是一種不同的生活。 我們中的很多人最終住在非常富有的房子裡,但非常不快樂、功能失調和有毒的家庭。 金錢並不能保證一切。
我崇拜我的養父,但我和我的母親就像油和水。 我們都有進步的政治觀點,但我們在許多其他問題上發生了衝突。 我不認為她真的想成為一名母親,這只是當時已經完成的事情,所以這給我們個人的火種增添了燃料。
我也覺得我不適合,因為我看起來不像我家裡的任何人。 我養母的皮膚很白,頭髮很紅。 我哥哥是金發碧眼的,所以人們說他長得像我父親。 但我有黑暗的特徵。 這讓我感到不安——就像我是一個不太適合這個圓孔的方形釘子。
改變一切的旅行
我對我的親生母親長大一無所知,因為我的養父母也對她一無所知。 但在 1983 年,我 23 歲時,我媽媽安排我們一起去愛爾蘭旅行。 她想讓我們去看看貝斯伯勒,讓我和我的兄弟得到關於我們生母的信息。 我的養父母認為我們有權知道。
我不能去旅行,因為我在佛羅里達找了份工作。 然而,當我的養母從愛爾蘭回來時,她讓我坐下來,告訴我她在家裡與一位修女的談話。 她對我母親了解不多,但我哥哥的母親顯然已經 16 歲了,當他們來帶她的兒子去美國時,她已經打了很長時間,據稱她打了一個修女。 強制收養在母嬰之家並不少見。
貝斯伯勒母嬰之家。 Mari Steed 的母親在這個家裡生下了她,然後將她送去收養。
我哥哥知道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他從小就以為自己被拋棄了。 這對我的養母來說是一次大開眼界的經歷,她流下了眼淚。 它也影響了我,因為我覺得我現在需要了解我自己的母親。 它在我的搜索下點燃了火焰。
尋找我的母親
那是 80 年代,所以這是互聯網之前。 我聯繫了我在報紙上讀到的被收養者權利組織,但他們無法獲得愛爾蘭的記錄。 直到 90 年代初,我才在愛爾蘭與網上的人建立聯繫。 他們為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我在美國提出了信息自由請求,以獲得我的完整移民檔案和出生證明。 然後我開始了一個網站。 一位住在倫敦的女性朱迪伸出了手。 她對家譜有著濃厚的興趣,多年來她幫助我尋找我的母親,在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英國之前首先搜索愛爾蘭記錄
我們找到了一個與我母親的出生月份和日期相符的女人,但這一年已經過了七年。 朱迪檢查了選民登記冊,發現了這個女人住在哪裡。 她還找到了一個曾經租給她的愛爾蘭人,他仍然經常見到她。 他同意代表我們聯繫。
我們知道這個女人已經再婚,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如果其中有丈夫或其他孩子,女人可能更願意保守收養的秘密。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尊重併後退。 但是有一天,這傢伙走近她的丈夫說:“哦,對了,美國有人在找喬西。”
她的丈夫直截了當地對他說:“那一定是她在愛爾蘭放棄的孩子。” 那是我們的腳。
我打電話給那個女人,從我聽到她的聲音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是我媽媽。 所以在 42 歲的時候,我終於第一次和媽媽說話了。
學習我媽媽的背景故事
第一個電話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它是如此簡單。 沒有尷尬,就像我們一生都在定期打電話一樣。 她告訴我,她每天都很想我,一直在等待和期待這個電話。 她在月球上。
後來我發現她是在機構照料下由修女撫養長大的,因為她自己的母親是在母嬰之家分娩的。 她去了一所工業學校,然後在科克的抹大拉洗衣店工作,直到最後,在 26 歲時,她被派往都柏林工作。
那是她第一次出現在開放世界中,她在那裡遇到了我父親。 如果你在沒有家人的情況下長大,那麼沒有人真正給過你愛和感情,是的,你會從第一個把你帶到舞池的帥哥那裡得到它。 我一點也不羨慕她。
當她懷上我時,她懇求修女們把我送到美國而不是愛爾蘭的工業學校,因為她害怕我會“像她一樣下場”。
我想她覺得她別無選擇,只能放棄我。 我理解她的經歷,因為我在 17 歲懷孕時也經歷過類似的情況。我的父母把我送到了產科,我的養母告訴我,“如果你帶著那個孩子回家,你就不會進入我們的家。”
當時,我不知道有國家對婦女的支持或嬰兒援助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也放棄了我的女兒以供收養。 我們後來在 1997 年重聚,現在關係密切。
如果這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如果你不知道你的選擇,我相信這就是強制收養的定義。 如果您不知道所有可用的選項,您就無法做出符合孩子最大利益的合乎邏輯的決定。
我和媽媽的關係
2002 年,我第一次見到我的母親。我們在希思羅機場外相擁時差點造成交通事故。 她對我的孩子感到非常興奮,其中兩個是我帶來的,因為在我之後她再也沒有孩子了。
2010 年,瑪麗·斯蒂德 (Mari Steed) 和她的生母喬西 (Josie)。兩人於 2002 年團聚,直到 2013 年喬西去世。
我們的關係感覺比我與養母的經歷要自然得多。 我們可以拿起並完成彼此的句子,我看起來像她,幾乎像她的雙胞胎。 這讓世界變得與眾不同,因為我覺得我在看著我的人,看著我來自哪裡。
我的養母對我追踪我的生母並找到她從來沒有任何意見。 她甚至遇到了她,並且有很多水廠和擁抱。 我很高興他們能在他們都去世之前見面。 2013 年生母去世時,我在她身邊。
我認為愛爾蘭的公眾終於了解了其母嬰之家的歷史,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通過乘坐出租車觀察到意見的轉變。 2002年,當我和我的生母告訴出租車司機我們的故事時,他回答說:“我認為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要小心,不要說得太公開。”
現在,20 年後,當我在那裡談論我為那些在國外被收養或被送到 Magdalene Laundries 的人進行的競選活動時,人們說:“現在是該該死的公開發表的時間了。”
Mari Steed 是收養權聯盟的美國協調員,該聯盟是一個位於愛爾蘭的倡導組織。 她也是一名作家,並為書籍做出了貢獻 愛爾蘭和抹大拉的洗衣店:正義運動, 和 糾正.
本文中表達的所有觀點均為作者自己的觀點。
正如對凱蒂·拉塞爾所說的那樣。
新聞出處:L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