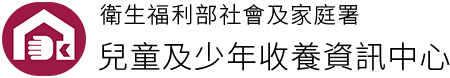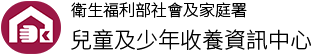【被偷走的人生番外篇】收養的艱難 法律如何保障「周子飛們」的兒童最佳利益?
【文 陳虹瑾/攝影 蘇立坤、翁睿坤/影音 陳建彰】2020/11/21
試想一個問題:倘若遭囚6年的8歲兒周子飛今日獲救,心理學教授戴浙能收養這個孩子嗎?
答案是:不能。
「當然不可能,收養絕對不能以學術研究為目的;收養動機必須是『組成家庭』,他(收養人)是真的要當他(周子飛)的父母。」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白麗芳指出,收養事件應將兒少最佳利益放在最高位,「針對每個孩子的狀況、需求不同,我們會優先考慮兒童利益,而不是說收養人有錢、有愛心、有社會地位,就適合收養每個孩子。」
白麗芳指出,若兒童成長於極端環境,收養人需要投注心力、長時間照顧,「孩子需要學習到什麼叫家庭?什麼是爸爸?什麼是媽媽?在這樣的情況下,能給孩子愈多時間的家庭,就愈適合。」
虐童案受害者普遍需要後續的療癒、教育,例如安排早療(早期療育)門診,甚至物理治療、語言治療等。白麗芳指出,台灣早療機制發展逐漸成熟,若這個年代有兒童被囚禁後獲救,會有更多專業人員介入協助,「例如:發展遲緩該怎麼教?更何況,他(周子飛)當年不是『發展遲緩』。他(獲救時)是『沒有發展』 ……,這種個案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療癒,但一定會有進步。」
周子飛當年被養父戴浙收養後,直接被安排進入幼稚園、小學就讀。如何看待這種「治療方式」?對此白麗芳直言:「直接把孩子塞進學校,現在的做法不可能這樣,一定是漸進式、安全的方式,讓兒童熟悉環境、學習與外界溝通,慢慢進步,經過評估之後,再逐漸進入小型團體、大型團體生活,孩子就不會那麼挫敗。」她也感嘆周子飛一路顛簸成長,「長到現在這樣很了不起了 ……,但過程實在太辛苦了!」
收養制度多項重大變革 早年僅有「契約制」
1986年3月29日,警方從囚屋裡救出周子飛,家扶中心隨後介入周子飛案,時任桃園家扶中心主任林平烘受訪時回憶,當時社工建議應暫緩戴浙的收養案,但據本刊調查,當時不過短短幾個月,戴浙就完成了收養。
談起台灣的收養制度沿革,白麗芳說:「那個年份,根本連社工評估調查報告的機制都沒有。」早期台灣的收出養制度並不完備,類似於純粹的「契約制」,在這種制度下,「你可以想像,會有(人口)買賣,會有出養方其實很弱勢、搞不清楚別人要如何對待你孩子,人家給你一筆錢,你就讓人抱走孩子。」
她看過光怪陸離的收養案,「很多人根本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收養,有的是家有身心障礙孩子,擔心老了沒人照顧孩子,所以收養一個孩子來照顧親生的孩子;或是長輩會強迫有孩子的一房,將孩子過戶給另外一房...很多人會利用收出養,做各式各樣奇怪的安排。」
1985年,《民法》修正規定「收養子女應聲請法院認可」,在這之前, 僅須收出養雙方合意訂定書面契約,即可到戶政機關自行辦理收養登記。修法後,收養行為由「契約制」改為「認可制」,除當事人合意成立書面契約,必須向法院聲請認可。
1992到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法通過,法院應將案子委由社工調查評估,「社工會寫一個調查報告給法院,法院再參考社工報告,決定要不要通過(收養案)。」白麗芳指出,相關法規陸續納入收養人財力證明、調查收養動幾等;2003年,《兒童及少年權利與福利保障法》納入出養必要性的調查,意即,法院認可收養案件前,必須調查有無出養必要性,在有出養必要性的前提下,才會進一步評估收養人的適當性。此外,裁定收養後,於法必須追蹤三年;全國各地陸續成立收出養中心,保存資料。白麗芳強調:「被收養的孩子有權利知道身世。」
2011年《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公布實施,規範禁止私下收養。「大家私下抱來抱去、約定來約定去,雖然有法院認可、社工調查,但很多事實已經發生了。」她強調,應站在孩子的最佳利益,此後收養一律透過機構安排,不能再「私底下約定」。收養機構如今會評估收養人的收養動機、收養後的計畫,諸如「孩子有困難,你要如何協助?」「你會和孩子談身世嗎?」
「現在(收養案)等那麼久,是有脈絡的,」白麗芳如今常聽到許多想收養孩子的大人抱怨,收養制度為什麼這麼麻煩?「案子出來了,你就會發現,(規範)是真的有必要的。」
新聞出處:鏡周刊